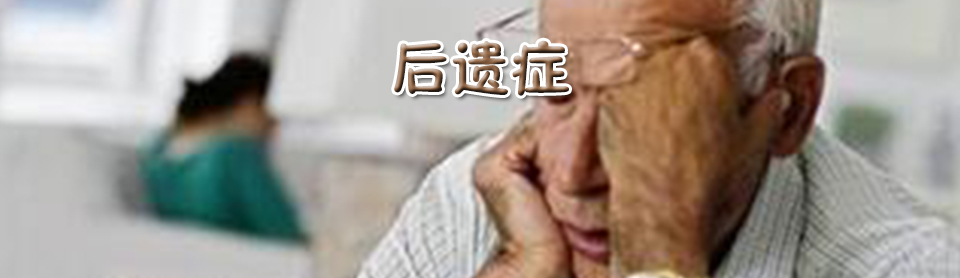我在儿研所抢救室的两天一夜
妈妈这个词,只是叫一叫,也觉得喉间哽咽。妈妈,最有力量的名字。
——《请回答》
在北京,为人父母,没有去过儿研所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小树出生的一年时间里,我跑过三趟,一趟比一趟刺激。
第一次腹泻,花块挂了专家号,因为病情太轻,专家连药都没开,直接建议回家多观察,等自然恢复;
第二次切痣,门诊小手术,切掉了那颗从出生就有的、长在脚底、一天天变大的黑痣。手术不复杂,但等在门外的几分钟很漫长,那是我第一次把小树留给陌生人,在他的哭声中关上门的那一瞬间,我几乎要落泪。
在那里,我还见到了黑痣布满半边额头和脑袋的孩子、褐色斑纹长满左腿的孩子,也目睹一位母亲哭晕在激光治疗室外,她的孩子当时正在里面嚎叫;
第三次抢救,因为血小板数值突然降至4,面临颅内出血的重大风险,我们在抢救留观室治疗了两天一夜。
期间受到的内心冲击,让我对妈妈这个身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
Part.1
冲进儿研所急诊抢救室的那天,是8月的一个礼拜五上午。
一个小时前,我在社区诊所拿到了那张化验单。因为发现小树脖子、脚侧突然密布皮下出血点,胳膊上还有淤青,我带他来抽血检查,本来只是想图个放心,因为挂号不太顺利,小树奶奶甚至最后关头还在劝我:要不别看了,肯定没啥事。
抽血室工作人员的尖锐声音划破了平静。
当我在十几分钟后回到抽血窗口附近,打算从自助机器上打印报告时,有人隔着玻璃急切喊我,“你可来了!”原来,他们已经反复拨打我的手机号,但由于信号不好,一直没打通。
“你家孩子以前血小板出过问题吗?”
“没有。”
“那怎么这么低!”
“多低?”
“4!都快没有了!”
难以形容那一刻的感受,像被一记铁锤蒙头敲过,我只记得,接过化验单的手一直在发抖。报告显示,血小板正常数据的最低值是,而小树的数值只有4,那个显示异常的箭头符号,无比刺眼。
回到诊室,大夫看到数据也急了:现在随时有颅内出血的风险,医院挂急诊。
这种感觉,就像本来只是准备探个军情,结果直接被推上一线,还是生死之战。
我的每一个细胞都紧张起来,赶紧去儿研所。不过,走出诊室,我先迎来了短暂的崩溃:站在昏暗楼道里给小树爸爸打电话时,还没来得及说情况,我先“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那是害怕失去最珍贵之物的恐惧。
再看到被爷爷奶奶带到门外等候的小树时,我百感交集。他看起来无比正常,见到我马上甜甜地笑,然后伸出小手,满脸急切地请求拥抱,嘴里发着清晰的“妈妈”,这是他新学会的词。
我难以想象,如果失去他,生活是否还能继续?不敢想,也不愿想。简单跟老人说明事态严重性,我直接开车奔向儿研所,小树爸爸在那里跟我们汇合。
车上,小树很烦躁。他又困又饿,在后排根本呆不住,一直哭着要来找我,而医院,在路边停了几分钟简单哄哄后,我狠下心来,让他继续哭,专注赶路。
我清楚,此时让他安全远远比让他开心重要——医院,我们被告知,他当时的嚎哭其实也很危险,容易引发颅内出血。
那场嚎啕大哭持续了40多分钟。哭声一层一层加重着我的焦虑,我脑子里浮现着各种可能性,最可怕的大概就是白血病,我甚至开始猜想可能是那些原因致病:他出生以来我们照顾得一直很细心,难道是那些我网购的衣服质量有问题?
更多时候,我在考虑如何应对。合格的中年人,永远会把更多时间用于解决问题,而非沉浸在情绪里。
我在32岁那年生下小树,过程并不算顺利,好在结果不错。我一直认为,他是上天送来的最好的礼物。堵在四环路上的那个中午,我脑子里重复着一句话:绝不把这份礼物还回去。绝不。
我甚至做了最坏的盘算,如果真的是重症,卖房也要治。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去换取小树的平安。
做好这份决心后,内心反而平静了许多。大概这就是母亲的天性,只要是为孩子而战,就会拥有惊人的耐力与战斗力。
到达儿研所急诊室时,小树爸爸已经等在那里。分诊,等待,小树看起来还是没什么异常。
但平静只是暂时的。当急诊室大夫说出那句“危重,马上去抢救室”时,我的心又沉了下去,抱起小树就冲向抢救室,速度极快。
现在想来,那应该是溺水之人扑向救命稻草的决绝。
小树被暂时诊断为血小板减少症紫癜,原因不明,大概率是免疫功能出现问题。第一步治疗方案是注射免疫球蛋白,观察指标,如果数据上升就安全了,如果没有,还要通过骨穿等方式,进行下一步检查。
在数据回升之前,小树都是危险的,要避免大哭,随时观察。在那间乱而有序的抢救室里,我签下了人生第一张病重通知单。免疫球蛋白属于血液制剂,输入后可能引发其他反应,因此也要签署告知书。
我注意到,急诊室里的这些文书,都是黄色纸张。标记着他们与正常纸张的不同。
我们被安排住进了抢救留观室。病房很简陋,除了六张病床、床头柜,只有两三把椅子,再没有多余的装备。盛夏,但房间里的空调显然被人关闭了,窗户开着——后来我知道,那是因为一些病重的孩子会怕冷。
小树的病床靠近走廊,斜对面就是扎针台。孩子们的哭声此起彼伏,很快,小树也加入其中,因为年龄太小,他只能扎头皮针,但他拒绝躺下,被按在台面之后,吓得嚎啕大哭,甚至把奶都吐了出来,小小的身体颤抖着,特别可怜。
我心疼不已,更难受的是,护士第一次扎针失败了,我强忍住怒火,把小树抱走哄了半天才又送回来。
“妈妈在,妈妈在”,我记不清自己那天把这句话说过多少次。以前在家时,小树每次从睡梦中惊醒时我都会这么说,我不知道他是否听懂,但我希望,在这个杂乱的、医院,他能更多一点感觉到安全。
Part.2
七小袋免疫球蛋白,分两天输完,输液开始后,我踏实多了。虽然还不知道效果如何,但至少,身处抢救室,小树的任何意外都能得到最快最好的治疗。
害怕他睡觉时翻身把针眼碰掉,我一直抱着他。我坚定着信念:我们在并肩作战,一定会成功的。
我这才注意到,病房里一直很安静,没有孩子吵闹,妈妈们聊天的声音也不大。是的,陪在病房里的几乎都是妈妈。
病房里椅子不多,仅有的几只都被绑定在固定位置上。小树爸爸无处可呆,打算在靠近隔壁床的椅子上坐会。但刚落座,原本陪孩子坐在床上的那位年轻母亲突然起身,举起一只白色喷壶在小树爸爸附近狂喷。
后来我们知道,那是消毒用的。因为那个7岁的小女孩,得的是白血病。
除了肤色苍白,那位小女孩似乎也看不出什么异样。她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喜欢看妈妈手机里的《小猪佩琪》。
而一个让我心生恐惧的巧合是,到那天晚上时,我发现,除了小树之外,这个病房里的孩子,全是白血病患者,且都是女孩,大多在10岁以内。
病房的安静或许就是这样来的。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寂静、闷热和消毒水味,是我对那间病房的最深印象。
那些白血病妈妈一直在消毒。她们每人都有一只同款喷壶,时不时就会举起来,清洁床沿、桌椅,甚至空气。
她们也会聊天,但多数时候语气平淡,似乎只是在讨论一场流感:“你家什么时候进舱?”“我家骨髓配对还没成功”“她爸爸今天刚给我生活费,一个月工资0,全给了”。
这种被变故击中后的麻木感觉,我以前当调查记者时见过太多了。
在那座山东小城化工园附近的“癌症村”里,那位刚刚因为喉癌失去父亲的儿子神色淡然,他的家人对于村子里变色的水、傍晚时空气里的异味都表现得习以为常;
在MH,那趟从马来西亚飞往北京的飞机失踪后,我曾经也在家属的房间里感受到平静,那位老人把桔子塞给我时的热情,像极了我平时在小区里遇到的普通大爷。
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人们往往会经历震惊、挣扎、平静的过程。麻木,是人类潜意识里对痛苦的隔绝,也是为了生存下去的隐忍和无奈。
但那间病房里,白血病妈妈们的聊天内容,还是让我觉得惊心动魄。
她们很少聊痛苦,聊正常生活被突然打断时的难过,更多的是经验交流,比如“进仓”费用的估算:孩子的体重后面加上“万”,就是手术需要的保守费用。
比如一位50斤的孩子,就要至少准备50万。
很多家庭掏不起这笔钱。
那位消瘦的87年东北妈妈说,为了来北京治病,他们已经找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借钱,很多人已经不接电话。女儿生病后她就辞职了,家里只靠丈夫每月0元的工资过。
他们至今没有准备好进仓的费用,甚至,她都无法确定,女儿是否会有进仓的机会——孩子爸爸已经不想治了。
缺钱只是一方面,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听说女儿接受骨髓移植后将来可能不能生育。“那还有啥用”,那位妈妈模仿着丈夫的话,在他看来,倾家荡产去治病,不如放弃,再生一个,反正他们也还年轻。
他们已经吵过很多次,甚至威胁过要离婚。毕竟,没有一个妈妈能接受放弃自己的孩子吧。
她语气平和得简直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我忍不住偷偷抬头看,那是一张没有光彩的绝望的脸。
“我从小到大都很顺利,以前别人都说我命好,哪知道是这样”,她继续幽幽说着。
我感觉到心酸,这些聊天都没有回避她6岁的女儿——那个小女孩就躺在她身旁,安静地看着手机里的动画片。
我不知道她能听懂多少,又会有怎样的心情?生存,死亡,放弃,这些对成年人而言都过于沉重的话题,这个小小的女孩,又能理解多少?
我不太忍心多看她。
第二天下午,那位9岁的白血病女孩在输液完成后准备离开。她被妈妈打扮得很漂亮,粉色裙子,白色凉鞋,双腿修长,瞬间从病人变成了少年宫里的舞蹈孩子。但出门前,她苍白的小脸上被戴上了一只硕大口罩。
而我对面的病床,是那两天的病房里最寂静的角落。那里躺着一位唐山来的十几岁女孩,刚刚经历化疗。偶尔路过时,我看到了一张苍白得毫无生机的脸,露在外面的胳膊,细得能看到血管,叫人不忍直视。她一直窝在床上,一动不动。
在那张病床的上空,我无比清晰地看到了死亡的影子。
Part.3
我的祈祷管用了。
输完两天免疫球蛋白,小树的血小板指数终于升上来了。周日早上拿到报告单时,我长舒一口气,终于重新恢复了对北京夏日的感知:树是绿的,阳光是明媚的,空气里有各种生动的味道。
我们逃一样离开了抢救留观室。空出来的床位,在十几分钟后就又被占上了。这里就像一座生命的流转站,病重的孩子们在此短暂交集后,有人痊愈奔向光明,有人继续坠入黑暗,甚至就此划上生命的句号。
而那些妈妈们的命运,也由此改变。
办理出院时,那位虚弱的唐山女孩被妈妈吃力抱下床,放进轮椅里,推出去做检查。
她妈妈看起来很苍老,两鬓头发已经发白,满脸疲惫。我们没有交谈,或许在她看来,我们是身处不同世界的人。
为她悲哀的同时,我也有些庆幸。我希望,自己永远不要步入那个世界。
抢救室的很多费用都是普通病房的两倍,我们住院两天,花掉近块,多数在医保报销范围之外。但只要能换来小树的健康,我什么都可以不在乎。
几天后复查,我去了儿研所的血液科门诊。
从分诊台到通往诊室的过道,密密麻麻全是人。等到号,我挤进去,排在前面的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妈妈,脸上写满焦虑。
她有两个女儿,老大得了急性淋巴性白血病,老二已经配对成功,符合骨髓移植条件。但这位母亲显然在担心,小女儿的身体是否能经受这样的手术。
我环顾四周,诊室里这些容貌普通的父母,平时可能就是坐在办公室的白领、开小店的老板、经营公司的商人、站在讲台上的老师……而当孩子被疾病袭击,他们也会被从日常的生活轨道中拖出,挤在这所医院里,被抹去身份,变成一张张奔走在化验室、病房、诊室之间的,焦虑的脸。
也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疾病随时可能摧毁一个幸福的家庭,而你永远无法被提前告知:它会在何时到来、以怎样的姿势出现。
唯一能做的,恐怕就是提高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
回到家的那个周日晚上,我和小树爸爸并肩靠在沙发上,又聊起儿研所的经历。
“我要加油挣钱了”,他语气坚定。
“还是先买份保险吧”,我立马回答。儿研所里那些因为重病而支离破碎的故事,让我心生恐惧。比起小树爸爸暴富这个虚无缥缈的flag,显然还是买份保险更靠谱。
事实上,保险是我以前无视甚至瞧不上的行业,但在儿研所的那一晚,当我听到40万、50万的医疗费用时,我居然开始下意识感慨:她们要是有保险就好了。
难怪有人说,生育会重塑一个女人的价值观。
小树暂时安全了,但他的警报尚未解除。因为不明确病发原因,此后的半年里,他不能接受疫苗种植,需要定期抽血复查——就在抢救留观室,我们遇到一位3岁女孩,紫癜治愈后一个月复发,原因可能只是妈妈得了流感。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为了健康的持久战。
我将倾力而为。
当然,我绝不打无准备之战。在密集学习育儿知识的同时,研究保险也成为我过去三个月里的重头戏。
我很快发现其中问题重重。保险条款复杂难懂,尤其是新手妈妈,最容易被销售抓住焦虑心理,购买并不实用的保险套餐。我的一位朋友,在孩子出生后就买了高端医疗险,一年保费一万多,最终只去看过一场感冒。
类似的案例比比皆是。
我打算做点什么。于是,在11月的第一个周末,我写下这篇文章,重启了这个只有35位粉丝的小小
转载请注明:http://www.hbshuangle.com/hyqf/47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