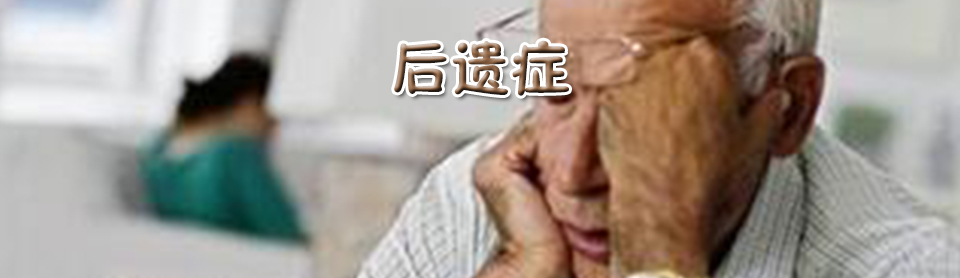杨刚之死一个左派女记者的悲剧
浩烈之徒:女记者杨刚
(一)
引子
杨刚,她曾经服务十年之久(-)的《大公报》并未将她淡忘。香港《大公报》网站上跟杨刚有关的文字至少有两篇。其中一篇题为《激情中飞扬的女记者——杨刚与〈大公报〉》,有记述文字如下:
杨刚出身豪门望族,却走上革命道路,一生清贫,无欲无求。她是一名出色的记者,一位知名作家,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一个运筹帷幄的外交家;同时,她还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她的《美国通讯》在解放战争期间,曾风靡一时;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她是十四位记者代表中唯一的女性。
但看过全文,我们不难发现,与其说这是一家新闻机构在纪念前辈员,不如说是一个宣传机关对其自身传统的确认。当年,正是经过杨刚主导的改造,这份过去“小骂大帮忙”“本质上反共”的报纸,终于转变了立场,“得以向进步方向发展”。这份曾经一纸风行中国四十余载的著名报纸,如今虽偏居港岛一隅、大陆上已经很难找到片纸,却仍在簇新的归地上继续在完成它所赋予的功能。
所以文章的煞尾也就不难理解。在这一段,《大公报》交代杨刚去世原因时语焉不详:“年夏,杨刚参加整风反右运动,6月9日以“金银花”的笔名发表诗作——《请让我也说几句气愤的话吧》,同年10月7日突然告别人世,享年52岁。”
突然别世
杨刚告别人世确实事出突然,她是自杀的。
应该是发生在六号的深夜、七号的凌晨,杨刚在自己的宿舍内吞下了过量的安眠药。六号晚上十一点以后,还有同事在单位和她交谈过。但是第二天早上,人们就发现她在宿舍自杀了。
杨刚当时所住的人民日报宿舍,具体地址是在北京市东城区煤渣胡同23号。这条胡同离人民日报当时的办公楼所在地王府井大街不远,走过去不过五六分钟,领导们安排宿舍时应该是考虑到方便夜班编辑们下班回家。叶遥是报社作品版面的编辑,当时也住这个宿舍。据她说,院子里一共住着五六户人家,和杨刚同住东跨院的有她的寡嫂沈强,其时也在人民日报工作。叶遥家在西院,她儿子那会才两岁,长得胖墩墩的,杨刚很喜欢他,过来串门时就抱抱,还送过高级的巧克力糖果。
杨刚姑嫂两人住在一起,也是相互有个照应。十一年前,沈强的丈夫、杨刚的哥哥、民国时期著名左翼报人杨潮(笔名羊枣),在国民党杭州监狱遇害;而杨刚的丈夫郑侃,虽然两人早在年便已分居但还是法律上的夫妻关系,也早在年死在了日机的轰炸之下,而膝下唯一的女儿郑光迪此时正在“老大哥”苏联留学。
正是沈强第一个发现了情况。7号一早,她去叫小姑子过早,这是湖北人吃早饭的习惯说法。和那个时代的其他高级干部一样,杨刚的宿舍很简单朴素,里外两间,外屋就当会客厅用;人们来拜访她,有时会发现桌上摆着一盆月季。没见回应,沈强进入卧室,发现杨刚整齐地穿着衣服,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情急之下沈强直接赶去单位求援。这个院子虽然都是同事,但是有人上夜班有人上白班,紧急情况找他们反而不方便。在那个年代,医院救护车、出租车都不太能指望,医院,最快的方式是去单位,何况又很近。于是,刚进单位的叶遥就听到沈强凄惨的喊叫声:“杨刚死了,杨刚死了。”
社长邓医院急救。简单检查过后,医生就宣布送来的这位中年女性已经死亡,她服用了过量安眠药。以如此方式离世,这不仅出乎所有杨刚身边同事、朋友的意料,可能她本人,刚来人民日报社的时候也不会想到。
此时,离杨刚来人民日报社担任副总编辑才过去两年。她来做报纸编辑是回归老本行,毕竟在民国时期,她已经是誉满全国的《大公报》名记者。到人民日报后,她先主抓国际部,后因一场车祸留下了一些后遗症,组织上让她改管文艺部副刊。
多年以后,人们回忆杨刚的时候,总会说起她的开朗、坦率、豪爽、热情和刚强。二十年后,她的挚友、后来以翻译英文巨著《尤利西斯》而为人所知的萧乾还在说,在杨刚女儿身上,他能看到一样的热情、爽朗。所有人记住的都是一个典型的无畏革命者形象。而自杀,在当时有着强烈的政治意味,身为高级干部的杨刚对这个“常识”不可能不清楚——事实上,正是因为杨刚的这种死亡方式,人民日报没有给她开追悼会。
杨刚之死让人们疑惑的还有,虽然这一年6月8日开始的“反右”运动之火已经在北京各大单位烧起来,《人民日报》正是这场运动的舆论风暴中心,但尚未涉及杨刚本人;而在此前的各类批判大会上,杨刚似乎也是风头正健。
杨刚之死在当时惊动了高层。《人民日报》最早的报人之一高集记述,杨刚去世的那个十月月末,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跟他详细询问过杨刚去世时候的情形和身后家人的情况。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当时是在北京工人俱乐部看京剧;在此之前,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等已经跟周恩来做过汇报。
关心杨刚死因的不仅有最高层,更有她的亲人、朋友、下属,不过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里谁又能向外吐露半句?他们都要等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陆陆续续撰文,回忆起心目中的杨刚来。吊诡的是,到了今天,杨刚和她的作品却成为了新闻史、文学史上的重要议题;而这些研究的原初动力就是杨刚之死留下的巨大谜团。作为后人,我们回望这件谜案,都希望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也许只有这样,才能从中获得一些什么教益。
车祸、丢失的笔记本?
胡乔木年在清华读书时就认识杨刚,建国以后工作又多有交集。年,杨刚女儿、时任交通部副部长的郑光迪请萧乾编《杨刚文集》,他们也请到了胡乔木作序。胡乔木作为党内“第一支笔”在这篇序言里对杨刚的评价完全可以被视为官方意见。胡一方面对杨刚作出了不低的政治评价,称其为“党和人民忠诚优秀的女儿”,另一方面也积极肯定了杨刚的文学成就,“富有热情又富有独特风格和识见”。而在说及杨刚为何自杀离世(他的用词是“逝世的特殊情况”)时,他解释有两个重要原因。一个是杨刚于年遭遇过一场意外车祸,结果导致其产生了严重的脑震荡,“一直没有能恢复正常”;再有就是,在年10月,杨刚丢失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笔记本。
胡的解释自有来处,这些最早也是其生前工作单位《人民日报》的内定说法。与杨刚同住煤渣胡同23号院的叶遥对当年杨刚死后的单位所作结论有记述:
邓拓在报社五楼大会议室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沉痛宣布杨刚去世,并说大约在10月初,她偶然丢失了一个重要的笔记本,心情不好,严重的脑震荡使她很痛苦。大家不要随便猜疑,不开追悼会了。
关于这场车祸对杨刚所造成的影响,《人民日报》的老人们后来回忆时都有提及。当年还是文艺部年轻编辑的黄岳军说:“年春天,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杨刚因车祸受到剧烈的脑震荡,休养了几个月后”,才“到报社来上班”。和杨刚有生活交往的叶遥用文学化的笔调地写到了她头疼发作时的细节,“她的身体不如过去了,有时双手交叉抱在额头上,用两个大拇指狠揉两边太阳穴”。杨刚告诉叶遥,吃药也不怎么管用,关键是记忆力变差了,“刚做过的事就忘了”。
组织上安排她去过南方的从化和杭州疗养,杨刚觉得不如在家好,头痛是阵发性的,过后仍可坚持工作。报社同事们便把需要她签发的副刊大样送到她家里。杨刚在外地疗养期间,萧乾正好陪同外宾到访,顺便也去看望了她。她对好友吐露说“担心自己成为废人”。不过萧乾也记得,过后不久,杨刚又乐观地告诉他说,她已经为报社写了两篇国际社评了,看来这个病是可以治好的。综合来看,这场车祸导致的后遗症确实严重,不过杨刚本人对工作的热情似乎不减从前。
这里有一个细节问题仍然需要探讨,就是车祸发生的时间。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几篇回忆都不一致。黄岳军说是年春,日后成为人民日报国际评论专家的蒋元椿是当时国际部的另外一个年轻编辑,他的文章《忆杨刚同志》也是写车祸发生于年春。不过萧乾编的《杨刚文集·杨刚年表》里记载的是年秋。老同事里,高集的纪念文章《杨刚在人民日报》一文发表较早,所记载的车祸时间却是年隆冬。
高集是年生人,年他37岁,在《人民日报》国际部担任西方部副主任,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在四十年代在重庆刚进《大公报》时就与杨刚共事过;那会高集就是《大公报》内部有名的左派记者。相比较而言,他对杨刚车祸的记载最为全面,可信度也最高。根据他的文章,车祸发生于年隆冬的一个早晨。杨刚下了夜班还没来得及休息,就赶去机场欢送一位外宾回国;就是在回城的路上,她所乘的小轿车与一辆卡车迎面相撞。杨刚住院疗养,一直到年春夏之交。出院之后,杨刚不再负责国际宣传,改管文艺宣传,“实际上过着半工作半休养的生活”。
官方解释杨刚之死可能的第二个原因是那个丢失的重要笔记本。有多重要?叶遥记述,杨刚去世当天,即有人跟她说,“杨刚丢了一个保密笔记本”“她的死可能与此有关”。金凤在文章里则直接说那是“一本周总理接见外宾时的谈话笔记本”。《人民日报》高级编辑钱江本人是《人民日报》史方面的专家,他父亲钱辛波也是杨刚的老部下。钱江撰写了一篇《杨刚自杀之谜》。根据他的转述,他父亲和挚友蒋元椿都不相信“丢失笔记本”对杨刚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一说,因为“以杨刚当时情况,她不大有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两位老人之所以如此结论,是因为和叶遥一样,在他们的记忆中,社长邓拓在会上说杨刚遗失笔记本是在10月初。依据高集的记述,从年下半年开始,医院回来后就开始主管文艺宣传,到年10月,已经不管国际部的工作快一年了,所以也不大有可能接触很多涉密事情。
关于这个丢失的笔记本,黎辛在年提供了最新的说法。黎辛是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编辑,年在中国作协担任副秘书长兼总支书记。他说,“事实是丢失笔记本在先,这个笔记本的捡到者将它交给了周总理,这杨刚是不知道的”。
黎辛的说法来自安子文。自解放战争时期开始直到年“文革”中被打倒,安在中央组织部长期担任副部长、部长。黎辛和安子文是在延安时期就熟悉的同志。根据黎在年发表的《我时常想起安子文》一文,不管是战争时期还是建国以后,安子文都对黎辛及其爱人多有人道照顾,彼此之间建立了革命友情和信任。因此,安子文对黎辛讲的话可信度很高。似乎是为了准确还原这件事情,黎辛在年不辞高龄又在第三篇文章里做了说明。三篇文章关于笔记本的说法基本一致,其中《我时常想起安子文》一篇又全是以安子文的口吻说出。转摘如下:
我问他:杨刚这样好而坚强的干部为什么突然自杀呢?安子文说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我说我不会外传的。安子文说:杨刚丢了一个笔记本,捡到的人交给周总理了。周总理和我商量将她调到人民日报社当副总编辑,一切待遇不变。可她免不了会想到这是周总理和党中央不信任她了。……其实,她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就算处理了,再没事了。我问是谁通知她去参加会的。安子文说:杨刚丢笔记本只有总理、我和中宣部的负责人知道。我问:杨刚的笔记怎么这么重要?安子文说:记了她与费正清(美国汉学家,抗战时期到中国,为美国新闻处工作)
的交往与联系办法。解放战争时,美国支持蒋介石进攻解放区。
所以,事实是,杨刚丢失笔记本一事发生于年调任人民日报社之前。调任就是一项低调的纪律处理,杨刚清楚不清楚这层含义,目前没有更多实证,但我们可以从杨刚死后人民日报社内部的一些反应来反推一下。杨刚一死,即有人跟叶遥说杨刚的死可能和丢失笔记本有关,邓拓在大会上又明确提及此事。金凤日后在文章中说,“她如实地向党组织报告了”“人民日报的党组织”和邓拓“根本没有对她在政治上有什么怀疑”。但对杨刚来说,她怀疑自己不受信任,不是来自人民日报,而是来自更高层。
依据高集的说法,年下半年医院回到报社一直到她过世,在这一年多的日子里,他就看不到她往日的“豪兴”了,人明显呈现出一种抑郁的状态。这种抑郁,高集归咎于工作上的调动,她的主管工作从原先的国际部改为文艺部的副刊,“她生性好强,多年来又是在炽烈的斗争和紧张的工作中度过的,一旦被迫处于闲散,心情上就感到受不了”。
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杨刚从原先的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岗位到《人民日报》主抓国际部的副总编辑,再到改抓文艺部副刊,也许第一次不足以让一个乐观的革命者产生什么怀疑,但到第二次呢?在因为失眠、头痛而导致的精神抑郁状态之下,杨刚可能就忍不住和邓拓告解一番。结果是,本来只有少数几个领导人才知道的事情,可能就在人民日报社内部也开始传了。
就这样,丢笔记本、出车祸这两件偶然的事情开始把杨刚推向一种不受信任的自我怀疑当中。这种境况,这一年来,她已经在自己众多熟悉和交好的同事、朋友身上一再目睹,并参与其中;但是她杨刚,一个浩烈之徒,会允许发生在自己身上吗?决不向她不认同的事情低头,五十年来,在她杨刚身上,毕竟已经一再发生过。
但这些就足以让她下定决心迈出最后一步吗?
(未完待续)
相关阅读第一位新闻发言人:每天都在为争取新闻自由而斗争伍豪先生关于外交工作的指导原则南京要风度,有人要站队鲁迅和冯至:五四的导师和学生學人文:一生的人文教育人文采访黄玉峰:批判性思维不是思想批判叶开:成为语文教育的“公敌”鲍鹏山:“一个读过书的父亲,会给另外一个世界”诗人李笠:十四五岁的孩子很可怕诗人蓝蓝:为了让孩子爱上阅读,我做了这些……史金霞:中国古典诗词里“很难看到一个真正独立的人”不得不记起我是中国人:刘勃谈传统文化这是魔的时代:电影《湮灭》的人文启示录人文短评为什么人人都爱张文宏?丁香医生和我们这次做对了多少,做错了多少武汉是什么?湖北是什么?湖北人又是什么?英雄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已被删)封城是决策,封路、赶人是什么?年轻人,干点什么不好呢?哀伤的,我记下了十件人文大事件恳请林少华教授完整陈述何为“深明大义”如何在朋友圈避免被举报的命运?反语言腐败专题徐贲:纳粹如何用语言改变了德国人的常识张维迎:语言腐败在中国已经无以复加(已删)谁该为汉语猥琐负责?一位语文老师这么说……脏话是一种绝妙的文化现象:另外一个语文老师的意见陈东东:现代汉诗的现代汉语“我是湖北人”系列我是湖北人:在上海思念一碗热干面我是湖北人:在黄冈乡下庆幸活着我是湖北人:去县城买房子的人我是湖北人:在Matters上写日记我是湖北人:返京之前我是湖北人:在孝感书店里写日记我是湖北人:湖北英山为什么抗疫这么突出?理解方方们的时代理解方方们的时代(一):武汉与红鲁艺(因为技术原因无发出)理解方方们的时代(二):悬崖边的树理解方方们的时代(三):年,木珍第一次去武汉人间纪事高福里春秋(一):著名翻译家林一安讲述上海石库门往事高福里春秋(二):著名翻译家林一安讲述上海石库门往事高福里春秋(三):著名翻译家林一安讲述上海石库门往事口述:在上海三林卖热干面口述:到崇明种田十二年非虚构:非典那年我高考:房产经纪人房其友的求学和工作故事入群交流,欢迎加我个人转载请注明:http://www.hbshuangle.com/zlxg/65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