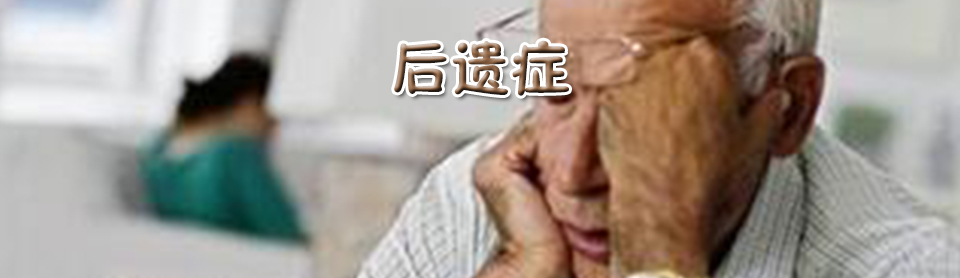鲁迅之孙当年ldquo叛逃rdqu
鲁迅之孙
当年“叛逃”到台湾后
周令飞,身份很特别,是鲁迅的长孙,也是三十多年前一起轰动的新闻事件的主角。
年,时在日本留学的周令飞随在日结识的台湾女友赴台定居,引起轩然大波。彼时国门初启,周令飞此举被许多人视为大逆不道的叛逃行为。对此,其父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记述了这一事件给周家带来的困扰。
斗转星移,中国巨变。周令飞当年的举动如今早已脱敏,他本人亦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回大陆定居,致力于其祖父思想与文字功业的传播。
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周令飞当年到台湾的第二年,即出版了《三十年来话从头》一书,此书随即也在香港出版。写作此书时,周令飞才29岁,中国也才刚刚从文革废墟中站起,艰难地摸索未来之路。他在书中回忆成长往事,记述求学、当兵以及做摄影记者的经历,虽然没有深刻的思想,但偶尔也有思考的锋芒闪耀。
作为鲁迅的嫡长孙,周令飞对自己身世、遭际的记录,为那个时代的中国提供了一份独特的档案。
祖父的遗产
周令飞出生于年。他有一个优越而快乐的童年。但此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家庭享有的崇高地位与优越的生活条件,是一个叫“鲁迅”的人带来的。
年后,周令飞的祖母许广平先后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以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务。这样的社会地位对应的,是公家配给的一辆苏联制三排式吉姆大轿车、一名公费司机、两名保姆。当时电视在中国是奢侈品,周令飞家有苏制的红宝石电视机。
住宅也相当可观。周令飞上小学二年级时,家里从北海旁的四合院搬到了公家配给许广平的一座高级、半洋式新居。整所院子有三十多个房间,许广平与周海婴的房间都是套间,周令飞与弟弟妹妹都有专用的卧室。
周令飞从小受的是精英式的教育。他上的是供高级干部与知名人士子女专用的幼儿园,幼儿园设备精良、师资雄厚。每个周六,他还可以与家人一道去欣赏“内部电影”,片子多来自国外。
周令飞小学、中学读的是北京景山学校,这也是一所特殊学校,他的同学中,有茅盾、萧华、罗瑞卿的子女。学校用的课本也与一般学校不一样,三字经、四字文与唐诗等古文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读。
根据周令飞的记述,自己家庭的朋友圈中,最要好的,是周恩来。
年,文革闹得正凶时,许广平去世。两个小时后,周恩来即赶到守灵室。他在守灵室中踱来踱去,满脸悲哀、沉重,还不忘问周令飞:“你们学校的‘运动’怎么样了?你参加红卫兵了吗?”
周恩来骨灰撒在大地上的做法,据周令飞的记述,是受了许广平的启发。许广平在遗嘱中说:“我的尸体,最好供医学的解剖、化验,甚至尸解,化为灰烬,作肥料入土,以利农业。”周恩来与邓颖超表示,日后也要效法许大姐,把骨灰撒在大地上,并且后来果真这么做了。
年,也即周恩来去世的前一年,他告诉周令飞一家,许广平可能是被害死的,但并没有说出凶手是谁。根据周令飞书中记述,怀疑的矛头指向了江青,后者指挥人抢走了鲁迅的全部手稿,导致许广平急火攻心,死于心脏病。而江青抢鲁迅手稿的目的,是想销毁其中关于她早年从影生涯的评论。
祖父的另一种遗产
除了社会地位与优越的生活条件,鲁迅还给周令飞留下了另一种遗产,那就是倔强的个性与批判精神。甚至,连“一个都不宽恕”的气质也遗传给了他。
一个细节颇能反映周令飞身上携带的鲁迅基因。
许广平在世时,郭沫若来作客。虽然早年郭沫若写文章批评过鲁迅,对来到府上的郭沫若,许广平仍十分客气。但周令飞心里却很气不过,他在郭沫若的茶杯里偷偷撒了一把盐。
周令飞的个性中有鲁迅的影子,但其青春期的精神资源却别有来处。他坦承自己对祖父的书看得并不精,对他精神影响最大的,是一个高干子弟。
高中毕业后,周令飞到东北当兵。在一次因阑尾炎住院手术时,他认识了高干子弟赵君。
这位也是军人的赵君,因工程塌方而被震坏所有内脏,切掉一边肺、一叶肝、四分之三个胃,脾脏、肾脏都重新修补过。医生宣布,他没有多久好活了。但是,凭借惊人的毅力与求生的意志,赵君不但逃出生天,还争取到了美满的爱情。
病床上的赵君与一位同样出身于高干家庭的女护士感情极深,但理所当然地遭到女孩父母强烈的反对,就连赵君的亲友也告诉他不要“害人”。在女友也打退堂鼓时,赵君写十余页的长信鼓励她。他同时积极锻炼身体。最终,赵君与女孩牵手,他本人康复后当了医生,两人生了个胖娃娃。
赵君的头脑更令周令飞佩服。他读书涉猎甚广,这在当时实属难得。六十年代的中国,各种翻译的言情小说、中国古典文学全被“红卫兵”列为“破四旧”的范围,不但禁止传闻,连持有都不可以。但在一些高干子弟中,这些书仍旧有市场。
腹笥甚广的赵君告诉周令飞某某书的重点在哪里、重要情节是什么、书中意义何在。周令飞视这位比自己大十岁的赵君为文学启蒙导师。
赵君更是周令飞精神上的启蒙老师。周令飞说,赵君是他见过的最大胆直率的人,他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很不满意。很多在周令飞眼中司空见惯的现象,被赵君批评起来就都不对劲了。“他这种不妥协、有头脑、不放任的作风,给我极大的启发。”周令飞写到。
周令飞中学毕业后参军,转业后到《解放军画报社》做摄影记者,这样的人生轨迹在当时令人艳羡。不过,周令飞在书中说,这一切全凭自己努力得到,与家庭背景没有任何关系。因为父亲周海婴一辈子都是极其讲究原则的人。他到日本后给父亲写信,直指父亲因为太讲原则,其实终生都是一个不快乐的人。
作为鲁迅的孙子,周令飞竟然因为家庭背景不够“红”,文革时申请当红卫兵不获批准。
祖母许广平的去世,是周家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周家不能再住原来的超大房子了,搬到一个比原来小得多的地方。周令飞与两个弟弟挤在一个房间里,由于放不下三张床,只好用书箱当床脚,自己买木板架在上面。在这种被周令飞称为“克难床”的床上,兄弟仨一住十二年。
周家在家里会见外宾的权力也被收回了。
家庭的变故,部队大熔炉的历练,特别是翻云覆雨的政治形势,让周令飞逐渐觉醒。“鲁迅的基因”爆发了,他开始拒绝参加各种充斥谎言的学习会。有一次,当编辑组长批评他时,他说:“你信不信现在的报纸?如果你真的相信,你可以批评我;如果你也有一分不信的话,请你不要硬拉我。”组长闻言无语。
周令飞对文革的反思与批判,即使今天看来也是颇具深度的。“今天的‘指令’转眼之间就作废了,明天的‘原则’后天又变成狗屁不如的废话,这种翻来翻去的变化,使得人民多少都有点‘神经质’。大家无法再用单纯的眼光来看人了,无论什么事情,人们都习惯考虑前因后果,计算利弊得失。谈话时一定各备一手,‘坦然相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林彪,到底谁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呢?各种各样的折腾,到底是革命呢,还是权力斗争?书中,周令飞这样问。
周令飞还写道,在日本留学时,他发现与台湾同学相处,不必高具戒心,精神上觉得放松许多。他为此感到痛心,“中华民族原是朴直而单纯的,人与人的关系原是亲切而和善的,十年文革,使人民的性格起了很大的变化,没有一个人敢于轻易相信对方。”
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朴直单纯变为复杂猜忌的情势,已经深入中国人骨髓,是“深入民族灵魂的伤痕”,只怕几代人都无法医好。而这才是中国最大的灾难、中国人民最深的苦痛,也给后人留下最惨的教训。
周令飞还说,如果祖父鲁迅活到今天,会不会成为旗帜,实在是个很大的问题。
悼鲁迅先生
巴金
十月十九日上午,一个不幸的消息从上海的一角传出来,在极短的时间里就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鲁迅先生逝世了!
花圈、唁电、挽辞、眼泪、哀哭从中国各个地方像洪流一样地汇集到上海来。任何一个小城市的报纸上也发表了哀掉的文章,连最僻远的村镇里也响起了悲痛的哭声。全中国的良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地悲痛的。这一个老人,他的一枝笔、一颗心做出了那些巨人所不能完成的事业。甚至在他安静地闭上眼睛的时候,他还把成千上万的人牵引到他的身边。不论是亲密的朋友或者恨深的仇敌,都怀着最深的敬意在他的遗体前哀痛地埋下了头。至少,在这一刻全中国的良心是团结在一起的。
我们没有多的言辞来哀悼这么一位伟大的人,因为一切的语言在这个老人的面前都变成了十分渺小;我们不能单单用眼泪来埋葬死者,因为死者是一个至死不屈的英勇战士。但是我们也无法制止悲痛来否认我们的巨大损失;这个老人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导师,青年失去了一个爱护他们的知己朋友,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代他们说话的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失去了一个英勇的战士。这个缺额是无法填补的。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样的一句话。然而我们并不想称他做巨星,比他作太阳,因为这样的比喻太抽象了。他并不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然界的壮观。他从不曾高高地坐在中国青年的头上。一个不识者的简单的信函就可以引起他胸怀的吐露;一个在困苦中的青年的呼吁也会得到他同情的帮忙。在中国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爱护青年的。
然而把这样的一个人单单看作中国文艺界的珍宝是不够的。我们固然珍惜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我们也和别的许多人一样以为他的作品可以列入世界不朽的名作之林,但是我们更重视: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在人类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勇敢的先驱。
鲁迅先生的人格比他的作品更伟大。近二三十年来他的正义的呼声响彻了中国的暗夜,在荆棘遍地的荒野中,他高举着思想的火炬,领导无数的青年向着远远的一线亮光前进。
现在,这样的一个人从中国的地平线上消失了。他的死是全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尤其是在国难加深、民族解放运动炽烈的时候,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导师,我们的哀痛不是没有原因的。
别了,鲁迅先生!你说,“忘记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忘记你的。我们不会让你静静地死去。你会活起来,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全中国人民的心里。你活着来看大家怎样继承你的遗志向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迈进!
年10月在上海
怀念鲁迅先生
巴金
四十五年了,一个声音始终留在我的耳边:“忘记我。”声音那样温和,那样恳切,那样熟悉,但它常常又是那样严厉。我不知对自己说了多少次:“我决不忘记先生。”可是四十五年中间我究竟记住一些什么事情?!
四十五年前一个秋天的夜晚和一个秋天的清晨,在万国殡仪馆的灵堂里我静静地站在先生灵柩前,透过半截玻璃棺盖,望着先生的慈祥的面颜、紧闭的双眼、浓黑的唇髭,先生好像在安睡。四周都是用鲜花扎的花圈和花篮,没有一点干扰,先生睡在香花丛中。两次我都注视了四五分钟,我的眼睛模糊了,我仿佛看见先生在微笑。我想,要是先生睁开眼睛坐起来又怎么样呢?我多么希望先生活起来啊!
四十五年前的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不管我忘记还是不忘记,我总觉得先生一直睁着眼睛在望我。
我还记得在乌云盖天的日子、在人兽不分的日子,有人把鲁迅先生奉为神明,有人把他的片语只字当成符咒;他的著作被人断章取义、用来打人,他的名字给新出现的“战友”、“知己”们作为装饰品。在香火烧得很旺、咒语念得很响的时候,我早已被打成“反动权威”,做了先生的“死敌”,连纪念先生的权利也给剥夺了。在作协分会的草地上有一座先生的塑像。我经常在园子里劳动,拔野草,通阴沟。一个窄小的“煤气间”充当我们的“牛棚”,六七名作家挤在一起写“交代”。我有时写不出什么,就放下笔空想。我没有权利拜神,可是我会想到我所接触过的鲁迅先生。在那个秋天的下午我向他告了别。我同七八千群众伴送他到墓地。在暮色苍茫中我看见覆盖着“民族魂”旗子的棺木下沉到墓穴里。在“牛棚”的一个角落,我又看见了他,他并没有改变,还是那样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小老头子,一个没有派头、没有架子、没有官气的普通人。
我想的还是从前的事情,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
我当时不过是一个青年作家。我第一次编辑一套《文学丛刊》,见到先生向他约稿,他一口答应。过两天就叫人带来口信,让我把他正在写作的短篇集《故事新编》收进去。《丛刊》第一集编成,出版社刊登广告介绍内容,最后附带一句:全书在春节前出齐。先生很快地把稿子送来了,他对人说:他们要赶时间,我不能耽误他们(大意)。其实那只是草写广告的人的一句空话,连我也不曾注意到。这说明先生对任何工作都很认真负责。
我不能不想到自己工作的草率和粗心,我下决心要向先生学习,才发现不论是看一份校样,包封一本书刊,校阅一部文稿,编印一本画册,事无大小,不管是自己的事或者别人的事,先生一律认真对待,真正做到一丝不苟。他印书送人,自己设计封面,自己包封投邮,每一个过程都有他的心血。我暗中向他学习,越学越是觉得难学。我通过几位朋友,更加了解先生的一些情况,了解越多我对先生的敬爱越深。我的思想、我的态度也在逐渐变化。我感觉到所谓潜移默化的力量了。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拿起笔并不感到它有多么重,我写只是为了倾吐个人的爱憎。可是走上这个工作岗位,我才逐渐明白:用笔作战不是简单的事情。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启发的。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梭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
我看得很清楚:在他,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他写的全是讲真话的书。他一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认错误,更不怕改正错误。他的每篇文章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他的确是把心交给读者的。
我第一次看见他,并不感觉到拘束,他的眼光、他的微笑都叫我放心。人们说他的笔像刀一样锋利,但是他对年轻人却怀着无限的好心。一位朋友在先生指导下编辑一份刊物,有一个时期遇到了困难,先生对他说:“看见你瘦下去,我很难过。”先生介绍青年作者的稿件,拿出自己的稿费印刷年轻作家的作品。先生长期生活在年轻人中间,同年轻人一起工作,一起战斗,分清是非,分清敌友。先生爱护青年,但是从不迁就青年。先生始终爱憎分明,接触到原则性的问题,他决不妥协。有些人同他接近,后来又离开了他;一些“朋友”或“学生”,变成了他的仇敌。但是他始终不停脚步地向着真理前进。
“忘记我!”这个熟悉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它有时温和、有时严厉。我又想起四十五年前的那个夜晚和那个清晨,还有自己说了多少遍的表示决心的一句话。说是“决不忘记”,事实上我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了。但在静寂的灵堂上对着先生的遗体表示的决心却是抹不掉的。我有时感觉到声音温和,仿佛自己受到了鼓励,我有时又感觉到声音严厉,那就是我借用先生的解剖刀来解剖自己的灵魂了。
二十五年前在上海迁葬先生的时候,我做过一个秋夜的梦,梦景至今十分鲜明。我看见先生的燃烧的心,我听见火热的语言: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但是当先生的言论被利用、形象被歪曲、纪念被垄断的时候,我有没有站出来讲过一句话?当姚文元挥舞棍子的时候,我给关在“牛棚”里除了唯唯诺诺之外,敢于做过什么事情?
十年浩劫中我给“造反派”当成“牛”,自己也以“牛”自居。在“牛棚”里写“检查”、写“交代”混日子已经成为习惯,心安理得。只有近两年来咬紧牙关解剖自己的时候,我才想起先生也曾将自己比做“牛”。但先生“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这是多么优美的心灵、多么广大的胸怀!我呢,十年中间我不过是一条含着眼泪等人宰割的“牛”。但即使是任人宰割的牛吧,只要能挣断绳索,它也会突然跑起来的。
“忘记我!”经过四十五年的风风雨雨,我又回到了万国殡仪馆的灵堂。虽然胶州路上殡仪馆已经不存在,但玻璃棺盖下面慈祥的面颜还很鲜明地现在我的眼前、印在我的心上。正因为我又记起先生,我才有勇气活下去。正因为我过去忘记了先生,我才遭遇了那些年的种种的不幸。我会牢牢记住这个教训。
若干年来我听见人们在议论:假如鲁迅先生还活着……当然我们都希望先生活起来。每个人都希望先生成为他心目中的那样。但是先生始终是先生。
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
如果先生活着,他决不会放下他的“金不换”。他是一位作家,一位人民所爱戴的伟大的作家。
年7月底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转载请注明:http://www.hbshuangle.com/fbsj/57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