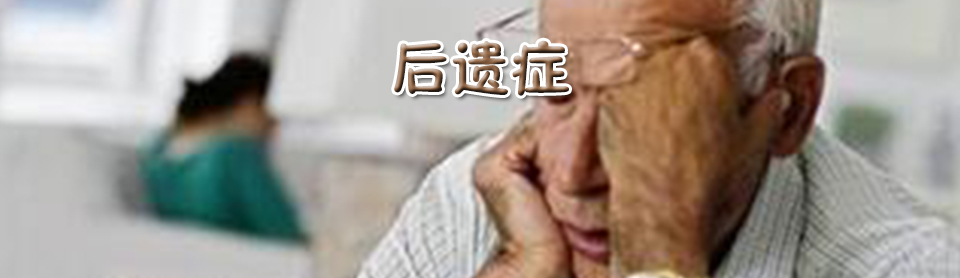我的手术后遗症
四周一片岑寂,
只有一缕清风飘忽不定,
来也无名,去也无形。
只要做了麻醉手术之后,我便不再恐惧死亡,因为没有什么比永恒的长眠更令人宽慰和幸福。
弗洛伊德无可辩驳地指出:在睡眠之中仍有潜意识的存在。与此同理,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死亡,一种将睡眠拉向无限的状态,将完全脱离人的意识而存在?鲜活的生命认为死亡遥不可及,沉眠的死亡也将生命看作难以想象的幻觉,这两个领域是否毫不相干?生与死的的对立关系或许是相互包含的潜在属性。德里达认为,人从出生的那一刻伊始,便携带着终将死亡这一可能性而暂存于世。蓬勃的生命力无论以何种形式萦绕在周身,甚至通过相片与影像的介质被刻录进电磁或数字的永恒领域之中,也丝毫不能削减这一令人恐惧的事实。在此之后,德里达更将个体的存在抽象为语言,思想,著作等实体形式的延续,人们在永无穷尽地对自我和他人的解构里暂时遗忘死亡的步步逼近,以此在解离、毁灭、重建、组合的循环中对抗整个世界。德里达没有直接触及存在的概念,毋宁说没有触及到存在的存在论概念,而仍停留在存在者本身。但我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中同样找到了精神的继承,即以解构的方式看待身体的见解。
人并不畏惧手术的过程,而畏惧手术对身体完整性的破坏,以及由躯体的残缺进而导致的精神异变。原始萨满崇拜中仍残留着对肉体和灵魂完整性的尊崇。自古以来,即便在祆教等二元论的体系内,肉体和灵魂虽然相互对立,两者依然紧密不可分割,互为存在的两种表现形式。古希腊的体液说则是把体液状态同精神疾病的诱因化作等号,中国历史中也不乏对破坏躯体完整性的疑虑而导致的悲剧。我们尽管不能完全否定此种联系,但这种"天然"的不信任感并不是人的本质属性,而同法律一样,仅仅是由人类自身赋予的概念。人不同于物体,也不同于机器,而是有灵。正是这种超越性让众人难以接受如零件更替般的冰冷机械感。然而在手术对过程中,我发觉手术对身体的替换和修补远不是部件修整那般简单。肌体的活力只有在非病态的条件下才能迸发,身体的修缮似乎驱赶走了病痛和死亡的阴影。处在完整性被破坏的残缺中,生命力如同饱受野火肆虐草原下的种子般积蓄着恢复的力量。虽然旧有的地貌无法复原,可并不妨碍葱翠的植被漫山遍野盛放。因此治疗过程中的虚弱被物化成更具普遍意义的薄弱,而死亡的可能性和恢复的可能性并存。要么继续活着,要么迎来死亡,两者在草原上周而复始,其实并没有什么差别,也没有什么值得惋惜可怜之处。治疗作为一次选择、一次机会、一次赌博而不是必胜的宣言呈现在患者面前。人和客体同样能被解构,不过这种解构不是物化的分割,而是将自我完全暴露在肉体解离的状态下,是在睡眠、麻醉和死亡进而延伸至清醒时的解构。在此情景下,人将突破肉身的限制,打破此生的壁垒,遨游于生与死共同构成的星空。只要曾闯入这一领域,这个人回到现实后便能突破对死亡桎梏的恐惧。这种观点倾向于将生死混为一谈,认为我们只能带着死亡的结局生活在星空的一侧,在另一侧则已死亡的形式继续“生活”。但我并不认为治疗驱散了死亡,也不是又人带着死亡的结局继续活着,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又将再次回到德里达的世界中。因此,我想再具体谈一谈这个话题。
死亡在生者的世界里虽抽象,但并非不可理解。另一侧的世界同样以生者的生活作为摹本。因此生与死两者固然不能分割开来,它们仍以某种隐秘的关联并存。麻醉恰好是分析这种关系的有力工具。麻醉首先是先验的,它处于可感的睡眠和不可感的死亡之间。因此麻醉过程可部分被事先预知,但也存在未知的感官步骤等待体验者亲自体会。这块中间地带恰似上述的星空,游离在两个世界之间,布满生和死的碎片。麻醉同死相近,两者皆由事实给定,终将如巨浪没过头顶,无法避免。麻醉和睡眠类似,两者均有可预见的终点摆放着现世的希望。麻醉是死的表亲,一者意味着片刻的知觉剥离,另者代表着永世的表层意识剥夺,一旦越过模糊的分界线,麻醉即化为死亡。麻醉是生的福音,它背朝死亡,而指向生的喘息,是人的求生欲在终场前一秒将比赛扳入加时的会心一击。麻醉时,一股矛盾感将油然而生。手术台之上,患者被推入无限接近地死亡的界限,医生们就在这悬崖边如履薄冰地操作,一点点地将患者推离万劫不复的深渊。麻醉在此世仅仅存在数秒,事实是,人类的意志在药剂面前毫无反抗之力。只需一瞬,透明的液体顺着针尖渗入细密的血管,心灵的门扉便就此紧闭。不同于常见的昏迷,麻醉好似电流的截断,以光速之势不留一分地阻断尚且清晰的意识,而昏迷则像水管里的水流,仅是亦步亦趋地归零。伴随着一股急促的注射胀痛,手术台的灯光在视网膜上都未曾逗留一瞬,患者就进入了生死的中间地带。麻醉无比接近永恒的死亡,因此带上了死亡的特征。麻醉期间,时间难以置信地扩展到无垠的维度,这种境界类似于禅定,超脱于三界,只身在空无一物的空间内伫立着,与天地相融为一体。在麻醉领域里不存在恐惧,我即是世界,世界即是我,而世界由生与死构成,因此我兼具生与死的属性,宛若造物主。由此而产生的满足难以形容,只有在宗教上才能找到些许足迹,圣徒、求道者、殉道者、圆寂者……如此纯粹的满足,唯有此种满足的满足,别无他想。麻醉是最底层的睡眠,任何外物的侵扰均无法动摇的沉眠,由此催生了一个无比漫长的梦。这个梦诞生于死亡的安定之上,超脱了有限时间的阻隔。梦是没有止境的,梦来自于无形,消失于虚无。我们很难界定梦的开端和结局,更多时候,梦就像记忆的片段,灵光乍现般出现,毫无征兆地戛然而止。但是梦也是没有尽头的,梦总遵循着它独特的逻辑无比逻辑地发展着,麻醉就是一场未完成的完整的梦。这场梦的来源有迹可循,也不存在割裂的记忆片段,它就像现实世界一样接续着变化发展,演绎着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知道这些体验,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麻醉后的苏醒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人体对麻药的耐受性各不相同,常用神经的通路也因人而异。在重新回到现实的世界并再次认识它的一分钟内,我度过了人生中最充盈又最迷茫的时刻。我的存在再次被世界接纳,历经了一个人生的断连之后再次得到连接,关于世界的一切不自觉地重新灌入我的脑海。我像一个懵懂的孩子,在数十秒间成长成人,从一具灵魂的空壳灌注为久经岁月的躯壳。再次认识现实的适应过程和意识到同那个世界的割裂同时进行,我无暇顾及周边的存在,只是默默地靠在床上无言地体会着这复杂的心绪,却又对此无能为力。如同梦将迅速消散,这种情感也在霎那间烟消云散,从此,我又成为了自己。口腔干涩,难以发声,麻药的效果仍残存着,身体难以动弹,一股无力的绝望顿时占据了我的心房。我十分怀念那个世界。
至于生死,我还需要更多时间去体会,也许在活着里,在麻醉里,在死亡里,不过我们总是将最好的留到最后。因为过了很久,我才发现,从那时起,支撑我活着的不再是对生的留念,而是对死亡结局的渴望,这就是我的手术后遗症。
.6.2于校图书馆的一隅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转载请注明:http://www.hbshuangle.com/zzbx/5666.html